通过社区生活的援助
我现在任职于NPO法人东大和(编者注:东大和为地名)自立生活中心(Center for Independent Living,简称CIL),CIL是一个以残障人士为主体、提供各项服务,包括维权、咨询和援助以帮助所有残障人士实现自立、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团体。为了让所有人在自己居住的地区过上舒心舒适的生活,首先必须要排除社会对残障者的歧视、偏见以及错误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比如说,经常有人说,“接受护理人员的照护,就不能算作是生活自立(一个人独立生活)”,那么让护理人员帮着做饭就不算是自己做饭吗?我们在历史课上学过,知道是丰臣秀吉建造了大阪城,但秀吉是自己建过城的柱子?或是搬运过建城墙的岩石呢?都没有。他只是“发号施令”而已,并没有亲自动手。那么我说“今天用冰箱里的胡萝卜和洋葱做个咖喱饭”,然后指示让护理人员帮忙做的咖喱饭就不能说是我做的吗?其实,稍微变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就会发现:不能因为身体的残障就把残障人士看作特殊人群和保护对象,他们作为一个人也是权利的主体。我们还会发现残障人士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造成的。我们希望通过残障人士实实在在的生活,通过他们和各色人等的接触,传递上述讯息。因此,我从2001年起扎根社区,持续开展相关活动,至今已有18年。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对残障者的歧视并未减少,这种歧视反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并以一种更难以应付的形式渐渐蔓延。过去常常看到有人明目张胆地歧视残障者,觉得他们“处处需要人照顾,很麻烦”。但2006年联合国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后,日本也于2014年批准该公约,并在国内制定了消除残障者歧视的法案,更因2021年残奥会召开的契机,开始宣扬“心灵的无障碍”。本以为一系列举措实施后残障人士能够活得轻松一点,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感觉却全然相反。
歧视的转变“善意的歧视”的诞生
最近看到的歧视的特征是,歧视者不认为是歧视,而是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残障人士好”,是出于善意的考量。比如说“出生前产检”,产检中得知胎儿有残障的孕妇中95%以上都会选择人工流产。这些孕妇大都认为“胎儿存在严重残障,不知道能够活多久,即便活下来也会备受歧视,降生到这个活着很艰难的社会反而是太可怜了”,于是以“为了孩子”的理由选择人流。接收残障人士的设施和精神病院往往也以“为本人好”为由将其隔离于地区社会之外,对残障人士进行“保护和管理”。事实上,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地方。因为自己居住的地区没有能够安心生活下去的场所,无奈之下才不得不选择了这些设施。
前面讲到的《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中,明确了:“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对合理性关照的否定”。“排斥”即是不接纳、让人走开,这比较容易理解。“限制”意为只对残障人士提出某些要求而不要求没有残障的人达到同样的条件。比如说“想上当地的学校,必须要由家长陪伴”这一条件。至于“区别对待”,是指“不听取本人的意见,只根据其他人的判断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同一集体中某些条件特殊的人”。在日本,不知为何“区别对待”不被认为是歧视,而被认为是一种“服务”。
・不是去保育园、幼儿园,而是去“儿童发展援助中心”
残障者的一生,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从自己的社区被隔离出来,被保护、被管理,被很多人抱怨“不生下来该多好”、“没有一点用处”,还一直被认为没必要延续生命(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完善相关法律、实现“尊严死”或“安乐死”)。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那是为本人好”。这个所谓的“为本人好”,真是让人无法反抗。因为抱有此种想法的人没有任何恶意,也是出于关心从心底里说出这些话的。大家都知道,美国曾经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有黑人专用的学校、公厕,公共汽车上也有黑人专座。通过平权运动,这些歧视性的措施已被废除。但是将残障者和普通人隔离的很多措施却被看作是一种“服务”而不是“歧视”,不同的是,残疾人“不能做和健全人一样的事情”。
如何消除“善意的歧视”
那么,要消除这种“善意的歧视”,或者说“自以为做得对实则是歧视的行为”,该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我真正开始困扰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的。然后,经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以隔离教育为本的现有教育制度下手进行改革!”日本过去曾实施过“推迟上学或免除上学义务”的措施,因重度残疾无法上学的孩子可以不去学校,但1979年实施“残疾儿童学校义务化”后,所有残疾儿童都开始接受教育,可是残疾儿童原则上必须上“残疾儿童学校(现在的特殊教育学校)”。我因为是1977年出生的,所以在残疾儿童教育义务化的大潮中,我违背教育委员会的”决定“而提出去当地的普通学校上学,一边与教委和学校抗争,一边在普通班级读到高中,并升入大学。这在当时纯属一个特殊案例。日本为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于2013年修改了《教育执法令》(第25号通知,文部科学省初等第655号),规定对于孩子上哪个学校应最大限度地尊重家长和本人的意愿。但是执行了数十年的“残疾儿童学校义务化”政策带来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现在仍有很多残障儿童理所当然地选择去特殊教育学校或班级就学。
另一方面,普通学校面向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始实施“心灵的无障碍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在已成为一门学科的道德课上,老师教导我们:“在街上遇到需要帮助的残障人士时,要热心地伸出援手提供帮助。”我每年也会有好几次受到社区学校的邀请,为学生们讲述残障人士在当地的生活状况。
但是如果有残障孩子跟其他学生一起在该学校上学,根本没必要特地使用教科书,或从外部邀请讲师帮助学生们学习与残障人士接触的方式。同年龄的孩子们被告知“为了让残障孩子在适合他们的环境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学习,最好还是去特殊支援学校”,这让他们感觉到“残障孩子身处和自己毫不相干的环境,是一个特殊群体”。于是,他们踏上社会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只停留在想象中,在街上突然遇到残障者时也不知该如何与他们接触,往往会装作没看见或不知所措,或在心里默念“自己身边没有残障者就好了”。
要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归根结底应该让各种各样的孩子从小一起学习、生活,不管有无残障。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碰到不会的或不擅长的事情,会的人伸出援手就能解决,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加以理解只强调用身体或通过体验来学习,在我看来就是欲速则不达的方法。
<<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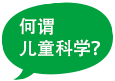

 NPO法人东大和自立生活中心原理事长。1977年生于川崎市。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患者。在居住地区学校的普通班级上到高中, 2001年3月毕业于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后在东京都东大和市开始独立生活,并在东大和自立生活中心开始从事与残障者生活有关的维权和咨询援助工作。现担任该中心理事长和“呼吸网”副代表、东大和市地区自立援助协议会会长、认定NPO法人DPI日本会议理事和东京融合教育项目代表等职务。2015年策划并参演了描绘依靠呼吸机生存的严重残障人士独立生活的电影《风说要活着》。创作了《吸一下空气吧》(现代书馆)、《我不再是残障者的那一天》(旬报社)等著述,2017年获颁东京都推进妇女活跃奖个人大奖。爱好旅行和清酒,座右铭是“不在于会不会,而在于做不做”。
NPO法人东大和自立生活中心原理事长。1977年生于川崎市。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MA)患者。在居住地区学校的普通班级上到高中, 2001年3月毕业于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后在东京都东大和市开始独立生活,并在东大和自立生活中心开始从事与残障者生活有关的维权和咨询援助工作。现担任该中心理事长和“呼吸网”副代表、东大和市地区自立援助协议会会长、认定NPO法人DPI日本会议理事和东京融合教育项目代表等职务。2015年策划并参演了描绘依靠呼吸机生存的严重残障人士独立生活的电影《风说要活着》。创作了《吸一下空气吧》(现代书馆)、《我不再是残障者的那一天》(旬报社)等著述,2017年获颁东京都推进妇女活跃奖个人大奖。爱好旅行和清酒,座右铭是“不在于会不会,而在于做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