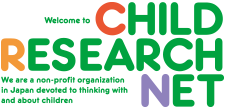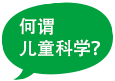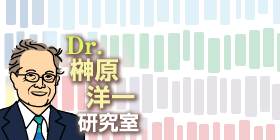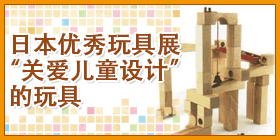姜 英敏(中国:教育学)
姜英敏的回应
读到山本老师的感想,我有两个意外。一是当年我提议山本老师借住到我亲戚家,不过举手之劳,没想到让他那么印象深刻。还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差点形成"极为特殊的关系、特殊的条件"(笑);二是制度性扶助在山本老师的视域中被划为"互相帮助"的范畴。
判断"共有"边界的能力
我请山本老师住到亲戚家,在山本老师看来也许是"随便的",但实事上绝不是。"共有房子"(至少他将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是我和这位亲戚之间的默契(暗黙の了解),有了对这个默契的判断,我才能够那么"随便地"、如同自己的房子一样地将房子借给山本老师住。默契,是中国式"共有"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准确判断自己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共有关系"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由此采取恰当的行为,是在中国维系圆满的人际关系的重要能力。所以,当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同学们:"认为自己有好朋友,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向他(她)借钱的同学请举手。"大家都会想想,然后有的举手,有的不举。却没人要先打电话向朋友确认能不能借钱然后再举手。这说明,同学们心中都有那样的"默契",这种默契,是让我可以当场借亲戚的房子给山本老师,也可以让山本老师的熟人在朋友不在的情况下把自己朋友的书借给别人,能不能顺利地理解这个默契,是重要的社会性发展的标志。而如果双方的默契感觉错位的时候,就会出现不愉快的场面甚至导致关系破裂。上一期中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梅,正是因为与百合的默契关系不同导致关系出现裂痕。
制度性扶助和人际关系中的互助
在我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把社会制度因素考虑进来,将讨论的边界限定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山本老师这次谈及中国和日本的差异的时候,把日本的制度性扶助作为与中国的个人之间的互助进行比较,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立论基础。
我之所以把社会制度排除在外,是因为想小心地剥离出"中国人之间不得不'共有'财产,互相帮助,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不健全,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靠不上制度。"这样的结论。在我过去组织过的中日学生之间的对话中也有日本同学说:"想借钱,为什么不向金融公司借?是不是中国没有小额贷款公司的缘故?"
但是,假设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香港、台湾这些社会制度健全的地区,人际关系的样态会不会产生变化?人们会不再形成"窄而深"的人际关系模式了么?至少从现在的文学、影视作品上看似乎也不是这样的。
到底该不该包括制度因素来重新构筑讨论内容?或许在下一期我们会有更深入的讨论,借以解决目前的困扰。
作者简介
 山本 登志哉(日本:心理学)
山本 登志哉(日本:心理学)
1959年生于青森县。在和服店做学徒后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攻读心理学本科和研究生。硕士期间,兼职做保育员时,对婴幼儿"所有"行为进行研究并撰写了硕士论文,荣获日本教育心理学学会颁发的城户奖。供职于奈良女子大学时期,曾作为文部省长期外派研究员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以研究婴幼儿"所有"行为的文化比较研究获得该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共爱学园前桥国际大学任教期间开始进行以零用钱为主题的日中韩越的共同研究,就此研究撰写的论文荣获中国朱智贤心理学奖。近著有《非语言交流的心理学:生活在偏差中的当代人》(与高木光太郎共编:東大出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