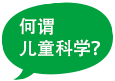儿童的社会性教育是儿童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儿童的情感——社会性发展为目标,以增进儿童的社会认知,激发儿童的社会情感,培养儿童的社会性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其目的是塑造儿童健全的人格,提升儿童生命的品质。[1]它需要教师关注儿童生命的本性,依据儿童生命的存在,采取符合其生命和身心发展需要与特点的方式进行,否则,难以在儿童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社会性教育也将流于形式且苍白无力。
一、两则案例分析
|
案例1: 为了引导大班幼儿学会和同伴交往的正确方法,一教师开展了“玩具要轮流玩”的活动。老师说:“有时候好朋友之间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就像这两位小朋友一样。”接着,老师请两位幼儿(一男一女)进行争抢玩具的情境表演。表演结束后,老师问小朋友:“这两位小朋友争抢玩具,对不对?我们来帮他们想想办法”。有的孩子说:“男孩应该让女孩”,有的说:“只给女孩子玩,不给男孩子玩也不公平,应该再找一个玩具”…… 教师打断孩子们的交流,启发到:“你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事情,你是怎么解决的?”一幼儿接着说:“有一次我玩一个玩具,哥哥也想玩,就拿着他的玩具对我说:‘我这个玩具很好玩,’其实他的玩具我玩过,一点也不好玩。我就没有答应他”。老师连忙接着孩子的话说:“像他这样行吗?生活中我们要学会相互谦让,玩具要大家轮流玩。” |
从上述活动过程来看,教师早就预设了活动的目标——“小朋友要互相谦让”,因此不管孩子怎么作答,教师最终都要回到目标上来。其实,适宜的社会性行为必须经过儿童自身的体验才能被认同并内化,与其回避、压制孩子的想法,倒不如让孩子充分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与体悟,再通过适当的问题情境,让孩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或自己认为合适的解决方法,从而学会用适宜的方式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这比教师牵强的总结要有效得多
|
案例2: 为了激发孩子爱妈妈的情感,老师设计了“红花送妈妈”的活动。老师先念儿歌,引出主题:“红花美,红花香,我要做朵小红花,要问红花送给谁?红花送给好妈妈”。“红花为什么要送给妈妈,什么节日快到了?”孩子们齐声答道:“三八妇女节要到了,所以要送妈妈大红花”。老师出示一朵大红花:“妈妈的节日要到了,我们做朵漂亮的红花送给妈妈,好吗?”于是老师示范做大红花的方法,然后孩子们回到座位尝试制作红花,最后孩子们拿着自己做的大红花围坐在老师身旁一起学念儿歌。老师总结到:“妈妈很辛苦,所以我们要爱妈妈,把做好的红花拿回家送给妈妈。” |
儿童的情感教育不同于认知教育,它的学习过程也不同于一般的认知学习过程,更多地强调感受、体验与理解。情动感受是儿童社会性情感形成的基础和起点。上述案例中的教师忽视了儿童情绪的感受与体验,只是一味地用认知替代情感学习,没有关心儿童的情感经验积累、体察儿童的情感体验,因此在激发儿童爱妈妈的情感上是无效的。
从上述两则社会性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现时期的社会性教育经常用一个确定的结论或普适的定义来诠释社会性教育的意义,关注较多的还是理性的结论,忽视非理性的感受、理解与体验,无视儿童作为学习者的生命存在与学习的生命特征,因而其教育的效果是无力的。
二、生命哲学的基本理念
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发端于叔本华和尼采,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狄尔泰、齐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尽管生命哲学家在理论主张上各有特色,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将关注的主题由自然物质世界转向了人自身与人的生命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割的生活。生命哲学家都不把生命看作是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而看作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即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认为哲学所应探索的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他们强调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生命的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特别是强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2]
从柏格森宇宙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即生命并非特指一个确定的事物,而是指一种永恒的力量、神奇的活力,一种生生不息的动力,到狄尔泰把“生命”直接回归到“人”身上,生命哲学家们关注到人的生命决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人是理性、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所以对生命意义的把握不能依靠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应把握意义关系,这种意义关系只有经过理解与解释才能把握。自然科学的教学适宜于追求因果关系,而历史及人文学科的教学则需要揭示意义关系。如狄尔泰认为生命以及生命的体验是理解社会——历史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永远流动的源泉,只有从生命出发,理解才能渗透不断更新的深度。[3]齐美尔从“生命比生命更多”“生命超出生命”两个命题出发认为,历史、人文科学是经验的、心理的,它们并无规律可寻,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人文历史科学一要关注体验与理解,“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那末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4]“只有当体验、表达和理解的网络随处成为一种特有的方法时,我们面前的‘人’才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5]二要强调直觉的方法。直觉就是直接意识,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由于每一个生命形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对生命的体验、理解也只能是直觉的,不可能从别的形式推论出来。正如齐美尔所言“我们对持续不断的生命的知识也许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我们所拥有的惟一的直觉知识。”[6]也正如柏格森所倡导的:为了认识外在的世界和自我,我们只须服从理智的思维习惯,进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就可以了;而要认识内在的生命、绵延,或真正的自我,则必须摆脱理性思维的习惯力量,走一条相反的路,即直觉之路。“直觉引导我们正是要达到生命的真正内部。”[7]